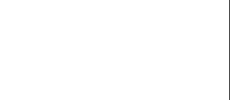定性比较分析法步骤(总结定性比较分析分为几种)
内容提要:
作为一种案例导向的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qca)于最近的二十多年中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普及和应用。本文对这一方法的研究逻辑、适用情境进行了介绍及分析,并就其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应用前景予以展望,提出了四个话题方向。文章同时介绍了该方法的操作步骤,以期将其引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拓展现有的方法论体系。
定性比较分析/研究方法/案例研究/集合论
作者:毛湛文
简介: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标题注释: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微博微信公共事件与社会情绪共振机制研究”(编号3&zd182)成果的一部分。
定性比较研究(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下文简称qca)是20世纪80年代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产生的一种针对中小样本案例研究的分析方法。qca最早由美国社会学者查尔斯·拉金(charles c.ragin)提出,在1987年出版的《比较方法:在定性和定量策略之外》介绍了qca,并将其视为是一种整合了量化和质化双重取向的研究方法。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发展,qca已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获得了广泛应用,集中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领域。
2014年,美国社会学协会将研究方法终身成就奖(又称拉扎斯菲尔德奖)颁给了查尔斯·拉金,以褒奖他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创立中做出的卓越贡献,这一奖项使qca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再次获得关注①。对于新闻传播学特别是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者来说,这一方法还比较陌生,运用该方法的研究文章也不多。但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有必要将qca引入到新闻传播学科中来,创新研究方法的路径。
基于此,本文将对qca方法的研究原理、分析技术、操作流程和适用于新闻传播分析的问题情境做一基本的介绍,以其引发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和参与。
一、qca是一种什么样的研究方法?
查尔斯·拉金在创立定性比较分析时,特意区分了qca的两重角色,分别是作为一种研究取向的qca和作为一种操作技术的qca(benoit & bojana,2009)。当它作为研究取向时,qca利用集合论和布尔代数开启了一种看待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新视角,并尝试融合传统的质化和量化方法,将其作为超越两者之外的研究取向。当它作为一项软件技术,qca则依据不同的研究需求,开发出相应的分析软件来进行逻辑运算,既应对新的问题情境,又节省人工的运算。因此,要充分理解qca的研究逻辑,就需要分别从以上两个方面认识这一方法。
(一)作为一种研究取向的qca
1.基于布尔逻辑探寻原因组合路径
qca依据的核心逻辑是集合论思想。拉金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许多命题都是系动词的表述,进而可以用集合之间的隶属关系来表示。例如,“发达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这一论述,就表明:发达国家这个集合是民主国家这个集合的一个子集。相应地,“新媒体技术的赋权能够带来网民表达空间的拓展”,转换为集合关系就是:新媒体技术赋权这个集合是网络表达空间拓展这个集合的一个子集。如果将研究问题或现象看作一个完整集合,那么引发这个问题或现象的诸多原因,就是这个集合的不同子集。基于此,通过一定数量的多案例比较,qca利用布尔代数的运算法则可以寻找到集合之间普遍存在某些隶属关系,展开因果关联的分析。
布尔代数的基本规定是:将某个变量出现或不出现用二分法表示为1/0,出现就取值为1或用大写字母表示,不出现则取值为0或用小写字母表示;用“+”表示“或”的关系,用“★”表示“和”的关系,用“=”以及“→”表示“推导出”。以上这些符号均用于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的集合关系的运算。例如,a★b=y就意味着当条件变量a和b同时发生时,就可以推导出结果变量y。
在对所有变量进行二分法处理后,qca围绕所要研究的结果变量,考察理想状态下存在多少种条件变量的组合,这样能够建立起一套逻辑真值表(truth table)②。真值表既可以反映出结果现象发生或不发生时多种条件的具体状态,同时还可以从中看出,多种条件出现或不出现之间的组合关系(configurations),进而得出这些组合是如何导致,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结果现象的发生或不发生(何俊志,2013)。
例如,导致现象d发生的相关条件变量有a、b、c三个,那么在d=1的情况下,相应的所有条件组合的可能就有2[3]=8种,其中a、b、c分别取值1/0表示各自发生或不发生。具体8种组合可以用如下矩阵表示。
从表1可以看出,这里列出的8种条件组合实际上形成了8个集合,分别为:{a=1,b=1,c=1}、{a=0,b=1,c=1}、{a=1,b=0,c=1}、{a=0,b=0,c=1}、{a=1,b=1,c=0}、{a=0,b=1,c=0}、{a=1,b=0,c=0}、{a=0,b=0,c=0}。而qca所要运算的就是,在一定数量的样本案例中,当d=1时以上8个集合各自覆盖到的案例占到总样本数的比例分别是多少。假设被观察的案例总数有10个,其中集合{a=0,b=1,c=1}出现在7个案例中,是出现频次最多出现的条件集合。这时,我们就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当条件a不发生且条件b和c都发生时,结果d=1发生的概率最高。
以上这个例子所描述的是qca运算中最为理想的情况,但在实际情况中所遇到的问题可能更为复杂。特别是当案例数量较多,且条件变量也较多的时候,就会出现矛盾组合的情况,即同一种条件变量的组合可能既导致结果发生,也导致结果不发生;同时还有可能出现,某一结果发生的条件组合中,某个单独条件可能是多余的,即无论这个条件是1还是0,最终覆盖的案例结果都是1。因此,具体的qca运算必须遵循“布尔最简化”的原则。这一原则是指:“如果在两个布尔代数表达式中只有一个条件的取值不相同,且它们得出相同的结果,那么这个取值不同的条件就是冗余的、可以删除的,这样就能得出一个较为精简的布尔代数表达式”(ragin,1987:26)。
借助“布尔最简化”原则,qca最终要找到的是解释结果变量发生的最典型、最精简、最核心的原因组合路径。特别是对于一些由复杂或繁多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案例结果,qca要做的是将各个复杂条件组合不断简化,排除冗余变量和矛盾组合,从而发现影响结果的关键因子和关键条件组合,建立相关的解释模型。用形象一点的说法表述,用qca解决复杂问题的思路在实质遵循的是一种“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思路——在“罗马”的方向可以得到明确判定后,即案例结果可以清晰地编码为1或0之后,考察并计算各条通往罗马的“道路”即不同条件变量组合的可行性和便捷性,通过在道路规划组合中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找到哪些或哪条道路是通往“罗马”的最佳路径。
2.面向多因诱致的复杂社会问题
qca声称是一种多案例的比较分析方法,但并非任何案例都适合用qca研究。qca对研究对象亦有特殊要求,概言之,它致力要解释的社会现象最好是“多重并发因果”诱致的复杂社会议题。也就是说,纳入qca分析的案例要具备成因“复杂性”的特点。拉金(1987:26)在发明qca方法之初即指出:“社会现象之所以复杂并难以解释,不是因为有太多的影响社会现象发生的变量(虽然条件变量的数量无疑也是重要的),而是因为不同的与原因相关的条件(different causally relevant)共同结合起来以某些方式产生一个特定的结果。”
这一论述其实暗含了以下两种情境:一是同一结果现象的发生,可能是由多种原因路径导致的,即y的发生,既有可能是原因a和b组合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原因c和d组合导致的,或者是原因a和c、d组合导致;二是因果关系并非是线性的、相关性的,而是复杂的、交织的,原因e的出现,可能导致结果y的发生;原因e不出现,结果y仍然可能会发生。
可见,qca分析的重心不是单个条件变量如何导致了结果的发生,它更关注多个不同的条件变量如何以“组合”的形式影响了最终的结果。因此,运用qca方法的研究要关注的核心问题应当是:面对“多重并发因果”的多个同类案例,导致案例结果发生的诸多复杂因素中,存在哪些因素的排列组合,这些因素条件的组合是如何影响案例发生的,哪一种因素组合起到的作用更大。
同时,在案例的样本规模上,qca也做了一定的限制,最好为中小程度的案例数量,在10个到60个之间为宜(bennett & elman,2006:470)。当案例数量过多时,用qca也可以进行分析,但不如传统的量化研究方法更有解释力。亚伦·卡茨等人(katz,hau & mahone,2005)的研究成果显示:回归分析在大样本(large-n samples)的研究中具有优势,但在中小样本(moderately large-n samples)的分析中,则难以提供有效的分析结论;在案例数量较少的情况下,qca比回归分析更具有研究优势。
3.超越量化—质化二元研究路径
qca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其对传统研究方法的整合与超越。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体系中,一直存在着量化和质化的分野。整体来看,量化取向的研究更关心对普遍问题的揭示程度,它建立在对足够多样本容量的考察基础上,立足在宏观的“面”上展开研究。无论是调查问卷还是内容分析,应用这些方法的研究往往更关注其得出来的结论是否具有更大范围的推广性,但这也相应导致它在问题的解释深度上存在先天不足。质化取向的研究恰好相反,它着眼于“点”上进行深入而细致的诠释,譬如就个别现象和个别田野展开有纵深感的分析。在大量细节的诠释中,质化的方法更依赖研究者自身的理论分析素养,这也被诟病为过于主观、缺少标准化的规范。
可以说,量化研究追求更多的样本量、更好的统计显著性、推断出更大的总体,强调客观性和研究的可重复性;而质化研究则强调个案研究和全面深入地理解研究对象,重视研究者个人在研究过程中的作用(陈阳,2015:51)。
是否存在超越量化—质化二元划分的第三种研究方法的路径呢?qca所做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它吸取了量化分析和质化研究各自的优势,希冀开辟出一种“中间道路”,建立方法的“中间视角”,是对传统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重要补充。因此,我们很难将qca轻易地归为量化研究或质化研究。
qca的分析并不是相关性分析,而是基于集合论的一种归纳和推演方式的分析,其数学基础主要是模糊数学,不同于传统统计分析的随机数学。传统定量研究的研究逻辑关注的是单个变量的“纯影响”,通过回归分析,排除他因,提炼出单个变量的真实影响效果,这致使研究者将工作重心放在检验单个变量是否在统计上显著(夏鑫,何建民,刘嘉毅,2009)。而qca关注的重心恰好相反,它所测量的变量往往更加复杂和多样,关注的是案例本身的复杂结构中蕴含了哪些条件,这些条件之间是如何相互组合、共同影响某个结果的。这是qca与传统量化研究的不同之所在。
此外,传统量化研究在研究之前便提出理论假设,然后设定一个研究模型以通过大样本回归验证这种假设。而传统质化研究则可以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理论假设,并基于某些特殊的个案不断地修正这种假设,并最终形成研究结论。qca在这方面更偏向后者,它在研究过程中密切关注个案,基于对个案的充分剖析,随时在理论假设和案例中调整切换。但也不能就此就将qca视为一种纯质化的研究。即使从方法的命名上看,qca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定性的研究方法。
一方面,qca在案例编码环节和运算环节,依然使用了量化研究的许多方法。比如,在具体操作程序上,qca遵循的是量化研究的逻辑思路,即按照严格规范的程序进行数据的采集、编码和运算。它可以同时处理多个案例,而且分析过程是透明的、可重复操作的。另一方面,传统的定性或质化方法中,特别强调研究者对案例的深度阐释,依赖主观描述的成分较大。但qca不同,它面对的往往不是单一化的个案,而是有着相近结构化特征的案例集群,这决定了qca所涉及的案例往往是多样本的。从某种程度上看,qca更像是近年来社会科学界倡导的“混合研究法”的体现。
4.借助建模寻求理论创新
通过呈现复杂因素内部的互动、组合情况,qca可以推导出多重解释路径,进而能够建立多个模型。由于扩展了解释的可能性,qca除了能够验证已有研究发现的常规因素组合外,还能够发现一些突破常识认知的偶然和非常态的因素。在qca的分析结果基础上,研究者可以从这些“偶然”和“非常态”因素追本溯源深挖下去,寻求能够解释这些因素发生的原因,而研究的创新点往往也是在这种偏离常规的探索中生发出来的。
qca对案例样本容量的特定要求(10-60个案例范围内),实际暗含了有一部分条件变量组合不能被观察到的可能性,即拉金(1987)所说的“有限的多样性”(limited diversity)。在实际分析中,qca既可以把没有观察到的案例排除在分析过程之外,也可引入一些没有观察到的但与现有理论不相冲突的“虚拟”组合,进一步简化假设(simplifying assumption)。引入没有观察到的个案,有利于理论模式的简化、证实、或证伪(李蔚,何海兵,2015)。最后简化的条件组合,往往能够概括所观察案例的共性特征,是一种建模的途径。
除了建模,qca方法还可以服务多重目的社会科学研究:一是数据统计对案例进行综合式描述,开展类型学的研究;二是检验已有案例量化研究中的相关性分析,发现“矛盾”和“异常”;三是对现有的某种理论进行评估,同时进行进一步扩展或完善,提出新理论;四是用来评估某个研究者提出的新理念、新方案和新猜想(马克斯,里候科斯,拉金,2014/2015)。其中,建模和发展新理论是qca应用中最高的层次。
(二)作为一种分析技术的qca
qca依据布尔代数所进行的集合运算,在条件变量较少的情况可以手工建构真值表完成,但随着变量数和案例数的增多,仅凭人工是不够的。拉金据此研发了服务于qca集合运算的技术软件,很快被应用于社会行动、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中。但同时,最初的qca软件也遭受到研究者的指责:它对变量的二分法处理虽简洁明了,但也过于武断绝对;实际案例研究中的许多变量比二元情形要更为复杂和多元。于是,拉金和其他研究者不断改进完善,以回应来自学界的质疑,继而发展了更多具体的分析技术和软件。本文就当前qca应用中最主要的四种分析技术给予介绍。
1.基于清晰集的cs-qca技术
在qca的最初设计中,无论对原因条件和还是结果条件的赋值,都是遵循布尔法最基础的1/0的划分。这时,导致结果发生的各个原因条件所形成的组合路径,都是这个结果集合确定的元素。因此,从集合的从属关系上看,原因条件形成的集合和结果条件的集合,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称之为一种清晰集的状态。
清晰集比较适合分析那些可以直接明确地进行二元划分的概念,例如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男性和女性、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党报和都市报、新闻报道和评论等。以上的这几组概念,在编码时都可以清晰地被判定为1或0。
2.基于模糊集的fs-qca技术
事实上,更多时候,一些概念在编码处理过程中,常常既不能完全归为1,也不能完全归为0,而是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基于这一现实,qca方法又发展演化出模糊集的比较方法(ragin,2000),引入了隶属度的概念。即依据每个条件变量与理想概念(1/0)之间的差距,进行定量的赋值,可以为0.4、0.6、0.85等等。然后,再运用模糊集合的算法进行隶属度值的计算。
在较长时间里,经典数学(包括精确数学和随机数学)在用来描述自然界多种事物的运动规律时,获得显著效果。但是,客观世界中还普遍存在着大量的模糊性现象;并且由于现代科技所面对的系统日益复杂,模糊性总是伴随着复杂性出现(李霖,2015)。清晰集所适用的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概念,毕竟是少数;更多情况下,概念具有无法进行二元划分的模糊性。例如,在描述世界各国新闻业的自由程度时,用威权主义/自由主义的二元变量显然不能概括实际的情况,大多数国家的新闻制度是介于二者之间,新闻自由程度的高低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时引入模糊集的测量比清晰集更为合适。
借助模糊集合可以用来评估交叉、包含、充分性、必要性等集合关系,进而可以计算每种条件变量组合对结果变量的解释力度。采用模糊集分析复杂现象时,研究者需要检测不同条件变量组合对结果变量的一致性(consistency)和覆盖度(coverage)。
如果用集合y代表案例结果发生时的集合,用x代表某种条件变量组合的集合。测量集合x对y的一致性,就是考察x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构成y的充分条件,即x集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导出y集合的结果。计算公式为:consistency(xi≤yi)=∑[min(xi,yi)]/∑(xi)。测量集合x对y的覆盖度,则是考察x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构成y的必要条件,即符合x集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证是达到y的唯一路径。计算公式为:coverage(xi≤yi)=∑[min(xi,yi)]/∑(yi)。覆盖度从0到1不等,越接近1越说明x因素的集合是达到y结果的集合的唯一路径(夏鑫,何建民,刘嘉毅,2009)。
3.基于多值集的mv-qca技术
多值集的分析与清晰集的分析原理相同,只不过是对条件变量的赋值,在0和1两种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将其赋值为0、1、2等更多的数值。这种多值的方法实际上类似于量化研究中的定类变量。这一技术的开发者克隆耐斯特(2004:4)认为交通信号灯的案例就是典型的应用多值集分析的情景,对红灯、黄灯、绿灯分别赋值0、1、2,就是一种超越二元变量的赋值。目前,研究者进行多值集分析主要使用的软件技术是德国两位学者开发的tosmana软件。
同时,mv-qca的分析结果中会呈现条件变量、结果变量和案例的对比情况,有助于发现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相互矛盾的案例。通常可以用它来检测模糊集分析的结果。目前,学界对这一分析技术的运用尚不普遍。
4.最新发展的t-qca技术
在拉金的模糊集分析中,只能是将各种条件的交集、并集或补集视为不同的路径。而在各种条件的交集、并集和补集中,看不到某些条件的出场顺序的差异对结果是否发生所构成的影响(何俊志,2013)。在实际案例分析中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条件a★b★c在导出结果时,与条件b★c★a所推导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这意味着条件变量发生的先后顺序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并没有被考虑进去。原因发生的时间顺序不同,最终的结果就可能发生变化。
鉴于此,在模糊集的基础上,有学者继而发展了时序性定性比较(t-qca,temporal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用“—”来标记每个条件变量的出场顺序,如c-a-b即表示条件c先发生,之后是条件a,再次是条件b(neal & panofsky,2005)。tqca技术关注了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时间这一维度,可以用来分析对原因发生时序颇为敏感的案例。
二、qca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
(一)为什么将qca引入新闻传播学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长期以来持有的是人文—历史—思辨的方法,规范的、遵循科学方法论的实证方法在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得到规范的确立和普及,也不过是最近三十年的事情(陈力丹,2011)。作为一种新的方法取向,将qca引入新闻传播学科,无疑将拓展现有的方法体系。具体来看,qca之于新闻传播的适用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对案例研究有着独特的青睐,例如新闻史研究中就有打深井、挖个案的传统。这个学科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往往也是以案例的样貌出现的,无论是媒体的报道还是媒介组织的运作,抑或是渗透社会生活的大量的传播现象、新闻事件,都适合用案例分析的思路进行关照和解剖。新闻传播学是一个依靠大量案例研究发展理论成果的学科,这一点跟政治学、经济管理学很相近。
但目前新闻传播的研究中,对案例的使用呈现出两种极端的倾向——要么是蜻蜓点水地举例,一个宏大理论思辨研究中被众多“例证”的论述语言占据,这种以论据出场的案例,常常是研究者颇为主观的引用,缺少科学上的论证;要么则是聚焦孤立、单一的个案,陷在案例的相关数据和材料中无法跳脱出来,研究可能遵循了严谨的量化或质化方法,做出了微观层面比较精致的分析,但所得出来的结论却往往限于案例本身而无法得到更广的推论。与以上这两种倾向的案例研究相比,qca则在跨案例、多案例比较的层面具有更大的应用前景,因为它强调在充分掌握案例材料的基础上和理论对话,并依靠案例去提炼、发展新的理论。所以,将qca引入到新闻传播学科,有助于摆脱此前案例研究较为陈旧的思路,同时可能带来理论创新上的突破。
另一方面,新闻传播学科中存在着大量的多重诱因形成的复杂现象,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特点来看,它相当契合qca对案例特质的要求。现实生活中,许多传播行为背后都存在复杂、多样的动机,加上客观社会环境的作用,能够解释传播问题的维度也相当多样。有学者(陈阳,2015:11)指出,因果关系是许多传播研究都力图证实的,但是传播关系里的因果关系更像一条“因果链”,它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分明,很少存在单一的变量关系(即引起某个结果的原因只有一个,或者某些原因只能引起一种结果),某个研究中的原因可能是另一个研究的结果。面对这种复杂的因果关系,引入qca的分析能够通过对多元原因条件组合情况的分析,无疑将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传播研究因果链条,在原因分析和解释上得出新的结论。
(二)新闻传播学适用于qca方法的研究话题
当前,国际期刊上应用qca方法发表的学术论文共有569篇,其中传播学科(communication & media)的论文仅有9篇③。而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应用这一方法撰写的论文更是凤毛麟角。不过,透过这些有限的文献的初步梳理,我们仍可以窥探到qca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几个代表性的应用方向。本文以适合qca的案例特征为依据,总结了如下几类导向下值得探索的研究话题。
1.事件导向(event orientation):网络事件与集体行动研究
新媒体以技术赋权的力量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结构,近年来层出不穷的网络事件推动了学术上对这一话题的思考。无论是社会行动还是网络事件,抑或群体性事件,不过是对这个话题不同的命名。面对网络事件,传播学中已有的舆论研究、群体传播可以提供理论资源,社会运动研究的相关理论也可借鉴。而社会运动正是qca方法被大量使用的一个研究领域。国内社会学界最早运用qca方法的文章,所关注的主题也是小区业主利用互联网展开抗争行动的因素(黄荣贵,桂勇,2009)。从目前来看,国内新闻传播界为数不多的运用qca方法的论文基本都集中在这个领域,是一个颇有研究价值的方向。
例如,李良荣、郑雯、张盛(2013)用qca的方法,研究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机理,从传播属性和事件属性两个维度进行解释研究。文章从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和已有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中梳理提炼出了10个影响因子作为条件变量,以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时差是否在24小时之内作为结果变量。通过qca分析发现,“公众共同的利益诉求”“事件发生地”“首发媒体”“首发位置”“中央媒体参与报道”这五项因素,构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关键成因。
马奔和李继朋(2015)则使用qca研究了邻避冲突类集体运动发生的条件,发现“风险感知和恐惧心理”、“信任缺失”、“政府应对失当”、“存在谣言”这四项因素的叠加组合,构成了邻避效应产生的必要条件。这篇研究注意到邻避效应发生过程中的一项与传播密切相关的因素,即谣言的影响力。文章发现信息不对称和公共决策的不透明是致使谣言产生的核心原因,这验证了传播学中此前关于谣言研究的通识结论。文章利用qca还发现了谣言这一因素会加大居民的风险想象和社会恐慌,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化邻避效应。
网络事件之所以适合使用qca,在于这类事件“复杂性”的案例特质比较明显。在网络事件和集体行动事件中,无论是线上、线下传播场域中多重主体的复杂建构,还是各方政治、经济力量对事件构成的复杂影响,抑或是事件在发生发展结局所显示的复杂过程,都体现了qca对研究对象提出的“多因诱致案例”的要求。复杂性特征决定了新媒体事件传播中的舆论态势不只存在一种解释路径,而是存在多个因素相互交织、共同牵制的解释路径。在以“事件”为导向的研究中,qca将会有更多的应用空间,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
2.组织导向(organization orientation):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传播的研究
当将社会组织作为研究对象时,其样本数量往往是中等规模的也是有限的,这就可以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纳入qca的分析对象。因此,涉及组织传播的话题同样适合qca分析。比如,有学者研究了17个ngo组织在挪威设置环境议题的能力,进行了跨国新闻报道的比较。此前的相关研究认为,挪威的ngo在纸质媒体报道上欠缺质量和深度。但该研究应用qca的分析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挪威的ngo组织的重心放在了专业知识的生产上,并非之前所说的温和的媒介行动(krvel,2012)。
以政府组织为案例对象的研究,可以与政治传播的议题对接。而qca在当前社会科学领域中,得到最多应用的就是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作为跟政治学有着交叉地带的政治传播,也适合使用这一方法。比较政治和政治传播共享许多相同的理论资源,可以借道取材或相互借鉴;同时,政治传播关注的许多话题都带有复杂性的特征,特别是放置在中国语境下的许多政治传播问题,勾连了意识形态、国家制度、政党、宣传体制、市场经济、社会历史等因素,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正在形塑着中国政治传播的现状。所以,以政府等政治组织为案例对象,用qca研究与之相关的政治传播话题,是颇为合适的。
以企业组织为案例对象的研究,则可以与传媒经济、公共关系、企业传播等研究领域对接。目前应用qca研究组织传播和管理绩效的问题,经济管理学已有成型的研究成果,可以迁移到新闻传播中。例如,有学者以央企集团为对象,分析了央企在管控架构选择上的不同,用qca考察了集团战略、制度改革、历史轨迹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丰富了企业组织架构和管控的理论(王凤彬,江鸿,王璁,2014)。
3.国家导向(nation orientation):跨国新闻传播问题的比较研究
从国际范围而言,回顾新闻传播学的经典研究,比较研究的色彩一直比较浓厚,特别在制度的宏观层面的比较研究,就更为丰富。新闻理论的经典著作《报刊的四种理论》就是对全球不同国家的新闻体制进行对比分析后所产生的学术成果(siebert,peterson & schramm,1963)。在全球新闻体制的考察中,进行跨文化语境的比较分析,已成为一种常规的研究思路,后期又衍生了像《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这样的著作。但是这一领域的对比研究,多是一种基于社会—历史—政治维度的描述和归纳,提出的理论模式在科学性分析上仍有一定欠缺。
反观qca所代表的比较研究思路,则是在“变量太多、案例太少”的情况下对少数案例进行比较性控制的方法。它不是微观的统计比较,而是一种宏观比较,国家或类国家的宏大系统的比较对象就很合适(高奇琦,2014)。因此,运用qca的方法进行全球新闻体制的比较研究,在建立模型方面或许可以弥补过去研究的短板。
不限于新闻制度比较议题,在全球化信息流动、交往、沟通日益密切的当下,中国国际地位的抬升,中国迫切需要与世界各国对话,“讲好中国故事”,也需要改善自身的国家形象。与之相关的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围绕跨国比较产生的新闻传播话题,也都可以运用qca的方法进行分析。
目前,关于跨国传播的研究,新闻传播研究者对qca的运用并不多,但在立足比较政治的跨国研究中,有一些使用qca的案例可以借鉴。例如,有学者从跨文化比较的角度,以清廉指数作为结果变量,用qca分析了39个国家造成腐败的文化根源,并尝试建模,提炼出了常规腐败模式、俄罗斯/韩国模式、中国模式这三种诱致腐败发生的不同模式路径(王程韡,2013)。还有学者聚焦26个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提炼出影响这些国家转型的7个历史遗产因素,进行qca分析,考察这些历史遗产因素对民主转型的影响力(唐睿,唐世平,2013)。这两项研究为跨文化新闻传播的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4.其他案例导向(case orientation):符合qca案例使用条件的研究
除了事件、组织、国家这三种导向外,新闻传播学的案例研究中还有其他一些适合qca分析的类型。比如,以中观社会行为(meso social action)作为案例,有研究者就从自我充权的角度对网络直播自杀案例进行了qca分析发现,在外力推动下的充权行为(如警方介入、网友介入、熟人介入等)能够阻止自杀的发生;即便当自杀当事人没有主动提供营救线索等主动自我充权行为时,警方、网友、熟人等其中任意一种外力充权行为也都有助自杀者生还;而网络直播自杀有助于自杀者进行主动的自我充权也就是主动求生(范毓洋,2015)。
此外,微观层面的个体(individual)和文本(text)也可以作为案例对象。虽然大多数情况下qca关注的是偏宏观和中观的案例类型,但这并不意味微观案例不适合qca(benoit & bojana,2009)。已有研究做了这方面的尝试:研究者用qca对移民群体的小样本案例做了探索性研究,考察在日本生活的中国技术移民幸福感形成的影响因素(李蔚,2015)。这篇文献发现,移民与移出国的社会联系有助于移民的主观社会适应,即与国内保持密切联系、维持较强的国内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弥合职业和未来发展的不安全感。这一结论同样超越了此前同类的移民研究。还有研究者以网站上188名欧洲科学家的简介文本作为对象,从简介的内容、例证、网络化和历史的角度提炼变量,用qca分析影响科学家使用互联网进行自我介绍的因素(michael & knigslw,2013)。这是一篇在微观层面做得较有新意的论文。
基于以上四个话题方向,可以发现,qca对案例的要求主要有三个:一是案例要符合“多因并发”的复杂性,即案例本身包含了较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原因结构;二是案例规模在10-40的中等程度,样本数特别小或特别大的案例都是不合适的;三是案例勾连的问题需要有理论的支持。因此,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案例对象中,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都适合用qca给予剖析。
三、qca方法操作的基本步骤
qca方法在操作中主要有四个步骤,可以用下图来概括,具体到每一步的操作,都有相应的规范性的要求。
首先,qca要求研究者不断地在理论假设和案例材料之间跳进跳出,提炼出要考察的条件变量。这是qca展开正式分析的准备性工作,但却是十分基础重要的工作。因为qca的前提认为:不同的因果关系路径也许会产生相同的结果。所以,在进行qca分析时要考虑因果关系发生的“特定情境”(马克斯,里候科斯,拉金,2014/2015)。
关于qca要分析的条件变量的设定,一方面要符合案例的内在结构,即每一个案例中应当包含了可供进行编码的条件变量;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变量也必须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即有充足的理论文献或前人研究论证过该条件存在的合理性,关注到过该条件对案例结果的影响。确定条件变量的过程是相当繁琐、但又十分基础的工作,需要在理论和案例之间反复对话。这一过程也是对研究者理论功底和案例材料熟悉程度的考验。
黄荣贵和桂勇(2009)在研究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时,首先对社会抗争的理论资源进行了详尽梳理审视,吸纳了集体行动理论中有关群体规模、群体异质性、闭合式社会结构、选择性收益等概念,以及社会运动理论的动员结构、怨恨心理、政治机会结构、社会网络等论述,进而才最终确定了案例的条件变量。
其次,qca需要重返案例材料当中,依据已设定好的条件变量进行编码。在清晰集分析中,对条件发生与否的编码为1/0;在模糊集分析中,对条件发生与否的编码则在1-0的区间内。在编码前,研究者需要根据设定好的条件变量,设定编码的具体依据和标准。而编码的过程更接近qca名称中的“定性”操作,即对每一个案例的条件变量做1/0的定性判断。这个过程执行起来是量化的测量,但实际操作中,需要研究者在收集到的案例质化材料中找到扎实、充分、详尽的证据指向要编码的1/0。换言之,我们可以将qca的编码看作是对质化案例进行标准化操作的过程。对于模糊集分析来说,在这一步中,还要对集合的隶属度值进行更细化的“锚定”。在确定数值后,研究者需要依据既有文献提供的理论或实际知识作为外部标准来对变量进行校准,不能以平均数或中位数作为校准的标准,而且连续型变量应尽可能利用专门软件来进行校准,避免手工计算出现错误。
第三,将编码表导入qca软件构建真值表。同时,研究者对每一个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一致性进行检测。这里的一致性检测包括了充分条件的检测和必要条件的检测。真值表能够呈现导致结果变量发生的所有条件变量的组合情况,以及覆盖到的案例数量。依据布尔代数的原理,在qca中对真值表进行逻辑运算(由软件在后台分析完成),获得分析结果。
这一步可以由研究者自行决定条件组合的复杂程度,qca软件可以提供复杂方案、中等复杂方案、简单方案这三种方案。用布尔代数确定简单的因果关系,其实就是在案例分析中尽可能减少到最少的因果条件。其中的关键步骤就是布尔代数的最小化(boolean minization),将案例描述缩减到对数据因果关联的最短表述(马克斯,里候科斯,拉金,2014/2015)。从而,在众多条件变量组合的分析中,找到最典型、最突出的诱因。这是一个不断简化和不断抽象的过程,也是一个探寻影响结果的最为核心原因的过程。
最后,完成建模后重新审视案例,进行案例的深度阐释和进一步讨论。同时,把概率组合的各种条件推广至其他案例分析中去,或建构新的理论假设。重返案例是qca分析的最终一个步骤,但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对此,有经验的研究者给出的建议是既要将研究案例进行逐个阐释(case-by-case interpretation),还要总结和解释跨案例的模式(interpreting cross-case patterns)(benoit & bojana,2009)。这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此前通过布尔最简原则获得的条件组合模型,能否将案例代表的社会现象和问题重新进行结构化分析?如果每个案例都是一个“黑箱”,研究者用qca获得的结论进行二次检验,其实是在回过头来重新解剖“黑箱”,检视结论模型和案例之间更细节、生动的勾连,进而从案例再回溯到此类研究的已有理论,做出修补或改进,有助于研究者获得新的理论发现。
从上述过程来看,qca分析虽然已经形成了相对明确、规范的操作步骤,且开发了应对不同变量编码需求的处理技术,但qca分析仍然不能摆脱研究者主观的判断和分析,不能脱离对每一个案例的深度剖析这个前提。qca的整个流程可以看作是对质化案例的一种标准化、规范化的操作,而基于布尔代数的逻辑运算借助软件也是为了提炼更精准的、有价值的条件组合,但以上流程的任何一个步骤,都需要研究者不断地在理论假设和案例材料之间不断对话、不断磨合、不断调整。这种跳进跳出的研究思路,是不能被任何软件技术所替代的。从这个角度看,qca方法实则对研究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它要求研究者对每个案例的经验材料有充分的理解和深入的分析;另一方面,它强调跳出个案、以整体眼光从样本中提炼具有普适解释力的一般性结论。
四、评价与总结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qca具有许多明显的优势。比如,它扩展了案例研究的维度和广度。就以往的案例研究来说,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整个社科研究中,案例研究主要停留在孤立的案例分析层次。打深井的、解剖麻雀的研究多,但能够提供结构化认识结论的并不多。qca方法实际上提供了一条对多个同类案例进行结构化比较分析的路径,它将点连缀成线,反而能够在问题成因、影响机制等问题上突破此前的研究困境。同时,相较于传统的量化和质化研究,qca结合了两者的优势,尝试打通楚河汉界,开辟超越这两种方法取向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qca得到普及和应用,实际上是契合当下社会科学方法中提倡多元方法、混合研究的一种趋势。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研究方法的分类不应仅局限在量化和质化这两大类上,应该有所扩展,尝试更多元的研究路径。当下社会科学界的方法革命,不只体现在qca日益被研究者接受,更多代表新取向、新范式的新方法正在得到运用。具体包括了abm(agent-based modeling,代理人基建模)、sna(social network analysis,社会网络分析)、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信息系统)、ism(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解释结构模型)、formal modeling(博弈论、经济学模型)、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等新方法和新技术(唐世平,2015)。这些方法同样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当然,qca本身也具有一些局限性。例如,分析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案例对象和条件变量的选择。增加或删除掉某个案例,也会造成条件组合发生变化。又如,确定条件变量的过程,是颇为主观和困难的事情。无论是多值分析的多元划分还是模糊集分析的校准过程都需要对变量进行性质的划定,而对变量进行定性划分缺乏客观而统一的标准仍是qca的一个软肋。另外,根据布尔代数的运算法则,如果有n个条件变量,最终就会有2的(n+1)次方个条件组合数量。每增加一个条件变量,将会是几何倍级别地扩增条件数量,也就增加了分析处理的难度。最后,qca虽然是服务于解决因果解释,但仍不能替代量化研究中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者对某一问题的因果关系考察,应该依据不同的研究情境选择合适的方法,将qca与已有的量化、质化研究更好地“融合”,应当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长期以来,国内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一直对案例研究和比较研究有偏好,许多研究问题的语境都涉及到案例分析比较的思路。而qca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适合案例的特征和类型,都能在新闻传播学中找到相对应的研究领域和话题。因此,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引入包括qca在内的更多新方法,相信将有助于促进学术方法的创新,提升整个学科的研究水平。
注释:
①拉扎斯菲尔德奖旨在奖励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该奖设立于1986年。详见网址:
http://www.asanet.org/sections/methodology_recipients_history.cfm。
②qca的分析单位是条件组合而不是案例,所以研究者需要根据不同的策略确定原因变量,然后以个案为单位对数据进行汇总,得到原因变量与结果变量的所有组合,这些组合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即真值表。
③查询应用qca方法的文章列表,可以通过compass这一专门网站获得各个学科领域的文章数量及摘要。详见网址:
http://www.compasss.org/bibdata.htm。
参考文献:
[1]阿克塞尔·马克斯,贝努瓦·里候科斯,查尔斯·拉金(2015).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定性比较分析法:近25年的发展及应用评估(臧雷振译).《国外社会科学》,10(40),105-112.
[2]陈力丹(2011).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创新.《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4),23-29.
[3]陈阳(2015).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范毓洋(2015).网络直播自杀事件中的自我充权与自我去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北京.
[5]高奇琦(2014).从单因解释到多因分析:比较方法的研究转向.《政治学研究》,(4),3-17.
[6]何俊志(2013).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模糊集方法.《社会科学》,(5),30-38.
[7]黄荣贵,桂勇(2009).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一项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社会学研究》,(5),29-56.
[8]李良荣,郑雯,张盛(2013).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机理:“传播属性”与“事件属性”双重建模研究:基于t95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qca).《现代传播》,(2),25-34.
[9]李霖(2015).《模糊中偶见清晰:纪念模糊数学诞生50年》.检索于
http://tech.qq.com/a/20150901/051646.html.
[10]李蔚(2015).飘摇的青春:在日中国“新”技术移民主观幸福感研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84-91.
[11]李蔚,何海兵(2015).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逻辑及其应用.《上海行政学院学报》,16(5),92-100.
[12]马奔,李继朋(2015).我国邻避效应的解读: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的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9(5),41-51.
[13]唐睿,唐世平(2013).历史遗产与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基于26个国家的模糊集与多值qca的双重检测,《世界经济与政治》,(2),39-57.
[14]唐世平(2015).超越定性与定量之争.《公共行政评论》,(4),45-62.
[15]王程韡(2013).腐败的社会文化根源: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社会科学》,(10),28-39.
[16]王凤彬,江鸿,王璁(2014).央企集团管控架构的演进:战略决定、制度引致还是路径依赖?——一项定性比较分析(qca)尝试,《管理世界》,(12),92-144.
[17]夏鑫,何建民,刘嘉毅(2009).定性比较分析的研究逻辑:兼论其对经济管理学研究的启示.《财经研究》,10(40),97-107.
[18]bennett,a.& elman,c.(2006).qualitative research:recent developments in case study methods.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9(1),455-476.
[19]benoit,r & bojana,l(2009).the case for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adding leverage for thick cross-case comparison.in david byrne,charles c.ragin(eds).the sage handbook of case-based methods.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222-242.
[20]cronqvist,l(2004).presentation of tosmana:adding multi-value variables and visual aids to qca,compass wp series 2004-20.published online,4.
[21]katz,a,hau vom m &mahone,j(2005).explaining the great reversal in spanish america:fuzzy-set analysis versus regression analysis.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33(5).539-573.
[22].r(2012).setting the agenda on environmental news in norway journalism studies.journalism studies,13(2),259-276.
[23]michael,b & knigslw,k.k.(2013).explaining cosmopolitan coverage.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8(4):361-378.
[24]neal,c & panofsky,a(2005).t-qca:a technique for adding temporality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vol.34,no.2,pp:147-172.
[25]ragin,c.c(1987).the comparative method: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6.
[26]ragin,c.c(2000).fuzzy-set social scie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本文刊于《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4期)